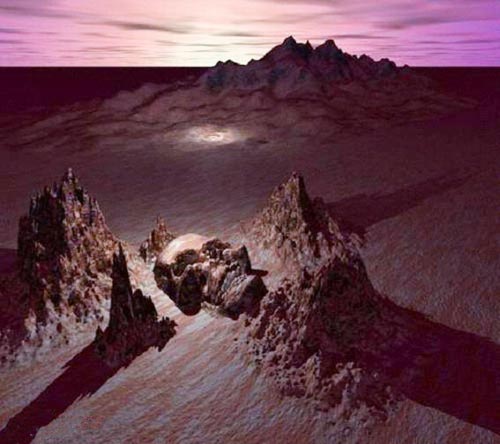
乌斯怀亚 (Ushuaia),是一个小城,也是一个海港,如果你打开世界地图或旋转地球仪要想找到它的所在可能要费一番周折,可我要说出:除南极之外,离我们最远的普通人可以正常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我想你会毫不犹豫地发现它的准确位置——南美大陆的最南端,位于麦哲伦海峡与合恩角之间的火地岛(西语:terra del fuego)上的一个小城,这些在中学地理课本也难得出现的名字,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真的会来到这里。 但当我确实已经站在那里时,时间已经是1998年的冬天,那里是初夏的季节。
据导游介绍:火地岛原为印第安人奥那族、扬甘族和阿拉卡卢夫族居住地。1520年10月,航海家麦哲伦发现了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时,首先看到的是当地土著居民在岛上燃起的堆堆篝火,遂将此岛命名为“火地岛”。1832—1836年间,自从英国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考察了火地岛后,该岛便名声大振。乌斯怀亚港也是南极科考船进入南极前最后的物资补给港。 在阿根廷完成计划的工作后,已是周末,当领队告诉我们火地岛游览的安排后,确实高兴异常,甚至有点激动。如果在国内,能去海南的“天涯海角”旅游,也总要兴奋一阵子的,更何况这里是“世界的天涯海角”呢。
飞机到达火地岛机场降落时,已是傍晚时分。一下飞机,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极具极地特点的海风,尽管已是初夏,但风里并没有多少温暖的感觉,既不像我们这里内地冬天的阵阵寒风,也没有青岛冬天海风的削面刺骨,但也失却春风的和煦。这风,没有间歇,没有变化,无处不在,包裹着你的身体,浸润着每一个毛孔,不是很冷,但使你整个人觉得像赤身裸体暴露在的空气中一样。温度也不高,和我们初冬季节大致相当,在5~10℃之间。

没有任何耽搁,我们就直奔预订好的酒店Tolkeyen hotel,那是一个由单层木石结构的房间组成的一个T字,外表看起来十分简单,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十分和谐。其实这是一个国际标准的四星级酒店,在当地知名度很高,也是离火地岛国家公园最近的酒店之一。
五个多个小时的飞行后,一行人等都觉十分疲惫,虽然天色还亮,吃过晚饭后,其他同行者还是早早休息了,因为导游告诉我们第二天游览的阿根廷国家公园,几乎要步行整整一天的路呢。
同行者中,我年纪较轻,当然精力要好些。而且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有时间,总是要把所居住酒店周围的环境熟悉一下,以免自己一个人活动时迷路。所以我并未马上休息,而是在酒店周围逛了一圈。

酒店是专为到国家公园旅游而建的,周围没有什么居民,也没有任何商业设施,更没有院落或围墙。酒店的右侧紧靠海滨,除周围空旷的绿地外,满目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酒店前,沿着海边有一条通往机场和市里的柏油路,通往国家公园等方向的几条路都是依地势修整的天然路面的步行道。站在酒店外也能清晰地看到隔着海湾的几公里外的机场里停泊或起降的飞机。
湛蓝的海面上,波浪汹涌,起伏的海水由远及近,翻滚到岸边腾起一个个白色的浪花。远处,偶尔能见到追逐嬉戏的海豚有一两只跃出海面。
太阳低低地斜挂在远处的天边,迟迟没有落下的迹象,尽管知道那太阳是在西北方向,但心理上总觉得那是南方,使我这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也不能不感到一丝别扭。
直到晚上十点左右天还未黒透,考虑到第二天的行程,还是按时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备好午餐,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就沿着山路向国家公园进发了。由于是国家自然公园,很少有人工工程,但可能考虑到多数游人的方便,依地势修建的天然路面的道路,尽管有点崎岖,但还算平整。由于实行了游客数量控制,路上的游人并不多,偶尔能遇上几个,但绝没有国内旅游点的那种感觉,仿佛置身于前人从未到过的蛮荒地带。
道路两旁被各种植被覆盖得严严实实,偶尔露出一些石块。同行者中,有一位是奇石的收藏者,每碰到石块都要停下来研究一番,也能遇到一些花纹奇特的石头,很像树木化石。有几块被他拿着把玩不已,自己拿不下时,也要我替他拿一阵子,看到它的兴致,当然不能推迟了,但过一会儿,碰到更好看的石头时,他总是把前面拣到的丢掉。
岛上树木品种繁多,生长着各种灌木和乔木,几乎没有认识的,但乔木以一种据导游介绍叫毛榉树的品种为主,并不高大。有些品种和我们这里的很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灌木还是乔木,几乎全是针叶的,这也可能就是达尔文所谓的为适应常年低温的气候环境、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吧。
在行进当中,也常常遇到一大片一大片枯死的树林,没有一丝的绿色。这些树木不知因何原因而死,也不知在那里矗立了多少年,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看到这里,生出这么一种感觉,只有看到西北沙漠中枯死的胡杨林或秦兵马俑时才有的感觉,由这感觉,不禁发出沧海桑田的感慨来!
在这个国家自然公园内,还生长着一种寄生树。寄生在较大的乔木上,寄生树长出的树根结成一团一团的,很像树上的一个个喜鹊窝。
有时,大片开阔的草地,还未完全变绿,地面上的枯草总是顺着极地风刮去的方向倾倒,草地下面的草根不知积累了多少年,也不知有多厚,像棉被一样,你高高地跳起来,落下去,没有任何声音,脚下也没有任何坚硬的感觉,软绵绵的,像跳弹簧床一般,只是没那么大的弹性罢了。
在路边,只要有植被,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蹲下来,扒开一看,就能发现十几种乃至几十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叶子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圆圆的,有长长的;有的开着黄的、红的、白的等各种颜色的花。还有一种蔓生在地上的小灌木,长满扎手的尖刺,结着一簇簇粉红色果实,形状很像迷你西红柿,有黄豆粒大小。我特意拍下了这种植物的清晰照片,回来后让几个做植物研究的朋友看过,只能判断它是一种生长在低温带的植物,但都无法准确说出它的名字来。
尽管风一直在刮,但也常常见到一处处山岭低处包围着的一小片湖水,如同一面镜子,并未被风吹皱,倒映着周围的树木、山峦,偶尔有几只水鸟漂浮在水面,尽管叫不出是什么名字,
但却给这一方水面增添了些许灵性。
最后到达公园的最南端:巴黑亚海湾(西语:Bahia Ensenada)。由于是海湾,和酒店边的海面比起来,风小了很多,浪也明显减弱。沙滩并不太宽,白白的沙,也并不细腻,但海滩上到处都散落着被海水冲上来的不知名的海草和从沙滩下冲刷出来的贝壳,尽管称不上美丽,但种类较多,充满着原始的野性。

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看腻了除了人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光洁的海滩,乍一看到这里,别有一番韵味。
在沙滩的中部,有一个木头搭建的栈桥,支撑栈桥的两排木头柱子上插满阿根廷国旗,大概表示和大陆相连的阿根廷国土的最南端就到这里了。我站在栈桥的顶端,极目远眺,尽管有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雪山海岛挡住了视线,但我知道,再有一千多公里,那就是我们祖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基地——乔治岛上的中山站。这也许是我一生中离南极最近的时刻。站在这里,我凝望良久…….。
再看那远处一座座雪山构成的岛屿,山腰的上下被一条整齐的水平线分开,上部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发出刺眼的白光,下部是茂密的绿色原始森林,这种景象更是平生难得一见的。
海边的石头上生长着一种黑色的海贝,在家我们叫海虹,但比我们这里的要大很多。我们一行几个十几天来,几乎天天吃烤肉,早就腻了。对于来自海边的食客看到海鲜和见到命根子一般,我们马上决定自己采集些,带回宾馆煮自己着吃。可刚一开始采,就被工作人员制止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个国家自然公园,除了你的脚印之外,什么也不能留下;除了你的快乐之外,什么也不能带走”。这是为了保护公园的自然环境而制定的制度,我们听了之后,不觉点头称是,也不好意思地把海虹重新放回到大海里。
离开公园时,那个采集了石头的同行者也悄悄地把包里的石头掏出来,放回到路边。
由于当时已是初夏时节,气温相对较高,只能看到远处海岛上的雪山,没有见到只有在冬天方可看到的海面漂浮的冰川及在自然中生活的企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转念一想,任何美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有缺憾的美才倍感亲切和真实。
晚上我们又去乌斯怀亚 (Ushuaia)的市中心,只用半个小时就逛了一圈,小城不大,据导游说,有五万人左右,大都以经营旅游用品和旅游服务业为生。
第三天离开这个海岛时,真有点恋恋不舍,仿佛置身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让人流连。
我曾想到:一个人,过去用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非易事,可现在,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日行万里,也并非难事。
我也想到了哥伦布,想到了麦哲伦,想到了郑和,是谁最先发现的南美大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他们的探险精神,依托现代科技,普通的人们也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甚至更远。
几年过去了,偶尔想到这火地岛,也不由地生出一种感叹:生活中充满偶然,就像这个火地岛,从没想到过但却有一天真的就来到了这里,而且一生中再来这里的机会也很少很少。许多事情也是这样,只有一次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并没有事先料到但却偶然出现了,却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出现第二次。
人生的轨迹时有重合,但更多的却是单行线,一去而不返。